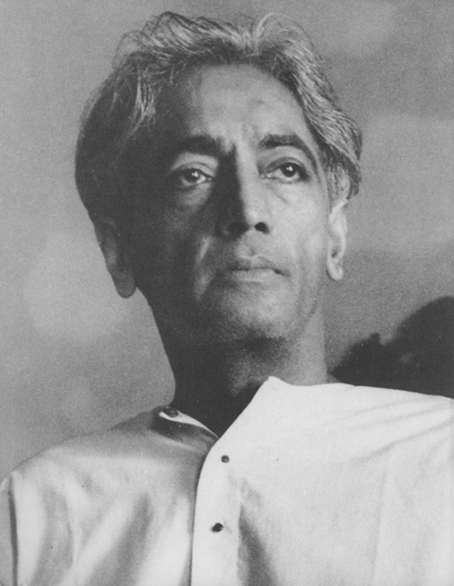
摘自《克里希那穆提传》
通神学会秘书长A.P.威灵顿先生提议让他们搬到加利福尼亚居住,那里的气候很适合肺结核病人疗养。一位友人——玛丽·格雷夫人马上安排了行程,并提供了两栋位于奥哈伊山谷的小屋,一套给威灵顿住,一套给两兄弟住。奥哈伊(Ojai)位于洛杉矶以北8英里处。
他们于1922年7月6日抵达奥哈伊,两个年轻人都很喜欢加利福尼亚的开放和自由,这跟印度和英国流行的阶级、种姓、种族意识完全不同。
尼亚似乎一度有所好转,更重要的是,兄弟俩终于可以独处。对他们而言,隐私从童年起就已经是奢侈品;而现在,他们几乎是与世隔绝了。他们的邻居只有威灵顿先生;一位沃顿先生——他是自由派天主教会区域主教——住在附近;此外还有19岁芳龄的罗莎琳·威廉斯,她是格雷夫人朋友的妹妹。克里希那穆提终于有机会独处了。
他常常独自一人漫步山间,穿越橘子林和灌木丛,爬上一处绵延的山脊,从那里俯瞰整个山谷。但是有一次,他一连数日被紧张笼罩,抱怨天气热得让人窒息。尼亚在一封给贝赞特夫人的信里描述了这次奇怪的事件:
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条遍布杏树和橘子树的狭长山谷里,每天头顶灼热的阳光都让我们想起阿迪亚尔,但是夜晚凉爽的风会从山脊的另一侧吹过来。从山谷低矮的尽头要走好远才有一条公路,连接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哥,绵延两千多英里,往来交通繁忙。但我们的山谷与世隔绝,无人知晓,宛若世外桃源,只有一条路逶迤而入。当地印第安人称这座山谷为奥哈伊,或“巢”,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把它当做一个避风港。
我们的房子在山谷高地尽头,除了威灵顿先生,几乎没有人在附近定居。他独自一人住在几百码远的一幢小房子里;克里希那吉、威灵顿先生和我已经来到这里将近8周了,我们放松身心,身体日益健康起来。美国自由派天主教会区域主教沃顿先生偶尔会来访,他在山谷里有一幢房子。还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女孩罗莎琳·威廉斯,会在附近停留一两周。大概两周以前,刚好我们五个人都在的时候,一件事发生了,我想向您描述一下。
17日周二的晚上(1922年8月),克里希那吉觉得有点累,而且有些烦躁。我们发现他的颈背中间有一个肿块,大概有一个弹子大小,有点像肌肉痉挛。第二天一早,他看起来似乎完全好了,但是吃过早餐之后,他却躺下来,浑身瑟瑟发抖,发出痛苦的呻吟。忽然他全身开始发出强烈的战栗,颤抖不停;他咬紧牙关,紧握双拳,想克制颤抖。这完全是疟疾患者的症状,但克里希那吉还抱怨热得要死。他的身体似乎在经历某种转变,好像是某些高于身体层面的东西在发挥作用。上午时情况更糟了,我坐在他身旁,他又抱怨热死了,而且说我们都神经兮兮的,搞得他很累。每隔几分钟,他就忽然从床上坐起来,把我们推开。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不清醒的状态下,因为他会滔滔不绝地谈论阿迪亚尔和那里的人,好像他们就在面前似的。后来他又静静地躺在那里,可是门帘、窗户发出的声音,甚至是远处林地传来的耕地声都会惊扰到他,他咆哮着要求安静。
我坐在旁边,但不是太近。我们尽最大努力让房间保持安静和黑暗,但是不可避免会有些轻微的响动。虽然别人很难察觉,克里希那吉却非常敏感,哪怕最轻微的响动都会让他歇斯底里。
……几分钟之后,这个可怜的家伙又开始呻吟,而且不久,他忍不住把吃下的东西往上泛。他整个下午都这样:发抖,呻吟,烦躁不安,不省人事,好像在承受巨大的痛苦。
……克里希那吉的情况好像更严重了,他看上去很痛苦,发抖和发热都加剧了,并且越发频繁地失去意识。当他好不容易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之后,又开始不停地谈论阿迪亚尔,他不断想象自己在阿迪亚尔。后来他说:“我想去印度!他们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我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他就这样一遍又一遍说:“我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儿。”差不多6点钟的时候,我们吃了晚饭,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我们吃完。忽然间整个房子好像充满了巨大的能量,克里希那吉似乎着了魔一样,用一种充满痛苦的声音说他一直知道该做什么。他从床上下来,走到房间的黑暗角落里,坐在地板上大声呜咽,说他想回到印度的树林中去。忽然他又说想一个人去散步,我们设法劝阻了他,因为我们认为他当时的状态完全不适宜夜间行走。他表达了自己想独处的要求,于是我们走到外面的走廊上,留他一个人在屋里。几分钟后,他过来找我们,手里抱着一个靠垫,离我们远远地坐下。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和意识,终于可以走到外面。但很快他的意识又一次离开了,身体留在门廊,坐在那里辞不达意地喃喃低语。
这时威灵顿先生像是得到一种来自天堂的灵感,他想把克里希那吉领到房子前方几码处的一棵小胡椒树下,那棵树有着精致的嫩绿色叶子,枝叶间缀满香气四溢的花簇。开始克里希那吉不肯去,后来却自己走过去了。
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星光闪亮。克里希那吉坐在树叶的阴影下面,无意识地胡言乱语,突然长出一口气,大声招呼我们:“噢!你们之前为什么不把我带到这儿来呢?”然后是一阵短暂的寂静。
接着他开始唱诵。他几乎已经三天水米未进了,又被过度的紧张折磨得疲劳不堪,因此我们听到的是一种非常疲惫的声音。他唱诵了在阿迪亚尔每晚都唱诵的经文。然后又是一阵寂静。
……我们坐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棵树,想知道是不是一切都恢复正常了。此时寂静无声,忽然有一刻,我发现一颗星在树顶闪现,我知道克里希那吉已经为“大一”境界(空性)做好了准备……现场好像充满伟大的神灵。我忽然想跪倒在地,顶礼膜拜,因为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心中伟大的主已经亲临。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但是所有人都感知到了他的降临。
……光辉壮丽的一幕持续呈现了几近半小时……然后,我们听到了克里希那吉的脚步声,看到他白色的身影从黑暗中走来。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天,那种发抖和半梦半醒的状态又在克里希那吉身上重演了一遍,但是只持续了几分钟,而且是断断续续的。整整一天他都躺在树下,保持入定的状态;到了晚上,他又像前一晚那样坐在那里冥想。此后,他每天都坐在那棵树下冥想。
我已经描述了我的所见所闻,但是我无法描述这次事件对在场的人产生的影响,因为这需要时间的见证。至少对我而言,充分理解我们有幸见证的光辉是需要时间的。现在我觉得只能用一种方式来度过我的人生,就是侍奉圣主。
对这些非比寻常的事件,克里希那穆提写下了自己的解释:
8月17日,我觉得自己的脖子后面疼得厉害,不得不将冥想缩短为15分钟。但那种疼痛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19日,体温上升了,我无法思考,或者说什么都做不了。朋友们强迫我上床休息,然后我几乎不省人事,但是又能感知周围发生的一切。我基本每天都是到了中午才恢复意识。第一天当我处在那种神志不清却能对周围事物感知得更清楚的状态下的时候,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最不同寻常的体验。我仿佛看到有一个人在修路,那个人就是我,他握着的那把镐头也是我,他正在击碎的那块石头是我的一部分,旁边柔软的草叶和大树还是我。我几乎可以像修路工人一样感觉和思考,我能够感觉到微风从树间吹过,草叶尖上的小蚂蚁我也能感觉到。小鸟、灰尘和声响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在这时,一辆汽车从我不远处驶过;我就是司机,我就是引擎,我就是轮胎;随着汽车远去,我与自己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我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山川、虫豸以及所有能呼吸的东西,万事万物皆在我之中。一整天我都沉浸在这种喜悦状态中。
……第二天早上(8月20日),情况几乎与前一天一样,我无法忍受房间里有那么多人……最后我徘徊到走廊,精疲力竭地坐了一会儿,稍微平静了些。我逐渐恢复意识,威灵顿先生把我叫去房子旁边的胡椒树下,我在那里盘腿坐下。坐了一会儿之后,我感觉自己飘离了身体。我能看到自己坐在那里,繁茂的枝叶在我头上。我面朝东方,面前是自己的躯壳,星星在我头顶之上,明亮清晰……我能看到自己的身体,并在它周围盘旋。
一种深邃的平和存在于空气中和我的体内,像是一种缘自深不可测的湖底的平和。我感觉自己的躯壳连同思想和情感就像湖泊一样,湖面涟漪微动,但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无法扰乱我心灵的平和。高灵降临与我共处了一会儿,然后他们就离开了。我感到无限喜悦,因为我看到了这一切,任何事物都无法与之比拟。我已经饮用过生命源泉里清澈纯净的水,我的焦渴已经平息。我以后再也不会口渴,再也不会置身黑暗,我已经看到了光明。我已经触及了能治愈所有悲痛和苦楚的慈悲;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整个世界……
在夜间的寂静中,克里希那穆提经历了一场转化体验,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日后,克里希那穆提依然长年累月地经历着这种痛苦的准备状态,他称其为“转化过程”。在这段痛苦的阶段,没有人考虑去为他寻求医学帮助,他和他周围的人都认为,这些遭遇是因为他的身体在进行灵性准备。而根据上古印度的说法,这是“拙火的苏醒”,意味着觉醒和释放的状态。
“觉醒”为何要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虽然兄弟俩很想知道,但是贝赞特和李德拜特在给他们的信里从未作出解答。尼亚曾经给出一个冗长的答案:
我觉得自己从未像那晚一样如此狂热地祈祷。仅仅是祈祷,而不是乞求让他减少痛苦,因为我们确信无疑:如非必要,神主们绝不会让他经历这种痛苦。我们都祈祷他不要记住这一切。但是要他不记住如此强烈的体验简直不可能,因为那是如此漫长的折磨。如果他记住这一切,我们担心那将会给他留下怎样一种可怕的烙印。
……他感到脊椎里炙烤难耐,想找一条沿溪谷蜿蜒而下的河流,把身体浸泡其中,以缓解灼热。我们很庆幸没有让他去。
那是5日(1922年9月)的清晨。夜晚时分,身体的这种准备状态达到了高潮,很明显,一部分并且很可能是大部分艰难的危险工作似乎已经结束。克里希那吉的忍耐、勇气以及那个伟大的场面带来了一种罕见而神奇的祝福。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威灵顿先生、罗萨琳德和作为他亲人的我,都幸运地分享了那份殊荣。那饱受折磨的一晚,似乎是在他躯体上打下的胜利的烙印。
克里希那穆提对待工作的态度也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化。带着崭新的力量和张力,他从1923年开始进行了密集的神智学巡回演讲,先是在美国,后来又去了伦敦、荷兰和维也纳。整整一年,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持续经历着痛苦的“转化过程”,不过只有跟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些事情。
满怀收获新知的喜悦和身负使命的激情,克里希那穆提周游了世界,在欧洲、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演讲。然而,排满了演讲、会面和会议的行程,对尼亚衰弱的身体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被诊断为重度肺结核。随着病情加重,尼亚写道:“我已经卧床四周,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我在死亡边缘几度徘徊……并且对此已经习惯。”
1925年7月,饱受疾病折磨的尼亚南达与哥哥结束了澳大利亚的游历,回到奥哈伊温暖的家。一场高烧让尼亚瘦得吓人,虚弱不堪,但是在气候干爽的山谷里修养了几个月,又接受了特殊的亚伯拉姆斯共振疗法(AbramsOscilloclasttreatment)之后,他好像慢慢好转了。
克里希那穆提非常担心弟弟的情况,甚至梦到自己拜见净光兄弟,乞求他们用他自己的幸福快乐来换取尼亚的生命延续。只要能让尼亚活下去,他什么都愿意做,因为“我感到他好像大限将至”;当被告知“他会好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如释重负,所有的担心都消失了,我很开心。”
贝赞特和李德拜特教义的基石是对密宗大师们的依赖,克里希那穆提年轻时亦对此深信不疑。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分界线是混乱的,幻象与圣主显灵对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是日常事件。但晚年时他说这些只是他的心理投射。
10月,贝赞特夫人给克里希那穆提发电报,要他陪同从英国去印度参加通神学会成立50年纪念大会。曼茨亚里夫人来到奥哈伊照顾尼亚,她从他们在巴黎的时候就开始支持他们,随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印度同伴罗摩饶。之前一直在奥哈伊帮忙照顾尼亚的罗萨琳德和拉加戈帕尔则与克里希那穆提同行。
对明星社成员而言,这些年来他们已经深信不疑尼亚注定是要伴随哥哥左右来辅助他的,这是伟大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命定的角色,尼亚的生命毫无疑问会延续下去。但克里希那穆提离开病榻上的弟弟时,还是非常不情愿。
1925年10月16日,克里希那穆提在纽约高谭酒店(theGothamHotel)给尼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的下一封信将从伦敦寄出,并说自己一直牵挂着他,从没忘记过他,他们彼此的爱远远超过世间其他事物,他们永远不会被分开。
然而另一场令人沮丧的事件接踵而来。从荷兰的赫伊曾(Huien)传来消息说,那里发生了一连串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启蒙已大规模进行,同时,乔治·阿伦戴尔犹如得到天启一般,宣布辅佐世界导师的十二位门徒即将横空出世。而年届80的贝赞特夫人1925年8月在奥门明星社的营地发布了一场冗长的讲话,确认了这种说法:“如同以前一样,他将选出自己的十二门徒……他已经作出选择了。”这些门徒中有李德拜特、贝赞特、阿伦戴尔、吉纳拉迦达沙、艾米莉女士,等等。

海伦·诺斯·聂尔宁
克里希那穆提早年的朋友
海伦·诺斯:在我开始阿姆斯特丹的学业之前,我跟母亲去了奥门。我母亲去参加维迪亚先生举办的课程,他当时是非常显赫的神智学家。菲利普·冯·帕兰德特邀请了克里希那吉,因为菲利普想将自己在那里的大面积房产馈赠给他。菲利普已经听说过克里希那穆吉,我想他一定是参加了巴黎的聚会。他邀请克里希那吉和他的弟弟做客,打算把土地馈赠给他。尼亚当时身体很弱,无法前来,所以克里希那吉一个人来了。我见到他那天,他已经到奥门几天了,菲利普开着车带他到处逛。他看到我在跟一个瑞典女孩比赛;我忘记我们在乡间参加什么比赛了,我代表美国,我的瑞典朋友代表瑞典,最后我赢了。赛后克里希那吉和菲利普·冯·帕兰德特走上来跟我交谈,我向克里希那吉要他的签名。菲利普见他兴致盎然,就提议到城堡一起吃个饭,于是我去了城堡,跟他们一起吃午餐。当时那里除我之外,没有其他年轻人,事情就是这么巧合。我成了让克里希那穆提一见钟情的年轻女孩——我年纪比较合适。
艾芙琳娜·布劳:第一次见到这个年轻人,你对他有什么印象?
海伦·诺斯:当时他身边还没有形成后来那种受人拥戴的热烈气氛。我对他的名声和言论一无所知,他对自己似乎也不是很有信心。他非常朴实,入乡随俗,独自一人来奥门找菲利普。菲利普是个很朴实的人,用简朴的方式招待他。他非常英俊,与我之前见过的其他男孩大不相同。他能够在荷兰停留的时间就只剩一周,而我会待得久一些。他利用所有时间和我在一起——我们在树林散步、骑自行车,或是坐菲利普的汽车外出,我记得那是一辆旧奔驰轿车。大约到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在石楠花田里一起散步,他坦承了对我的爱。他非常害羞,用手帕遮住脸。我们坐在石楠花上,他给我讲了他深爱的弟弟、他唤作“阿妈”的贝赞特夫人以及艾米莉女士,并说他们是他最亲爱的三个朋友,然后将我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当然会是这样,我们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一些很不寻常的东西。
艾芙琳娜·布劳:他跟你说话的时候遮着脸?
海伦·诺斯:他太害羞了。他离开奥门后——他必须回伦敦然后去印度——在给我的第一封信里说:“回想起来我是多么的羞涩。”他还说:“你与我对这件事的感受不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留着这些信。它们如此纯洁,如此高贵,如此美丽,如此动人,而且它们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部分。
艾芙琳娜·布劳:克里希那穆提表达过他个人对婚姻的看法吗?
海伦·诺斯:没有。我们从没有考虑过这个。而且那时我们虽然很亲密,但我不记得有过任何爱抚、拥抱或接吻。这很奇怪。我从没想过:“噢!我绝不能这样!”我们也从没想过:“我们绝不能这样!”我们之间有的只是一种吸引,一种心灵的交会。我是在17岁时经历那种感受的,虽然当时我还只是一个青涩的美国女孩,但我确实经历了那种感受,我有时会品味它意味着什么。
艾芙琳娜·布劳:你是说你们的友情或感情并没有涉及身体接触?
海伦·诺斯:一点没有,完全没有。但温馨而深入,甚至充满激情。这很奇怪。那时他的爱意如潮水般奔涌,他想让我和他在一起。遇到我之后很快就要离开,这让他非常沮丧。我们在荷兰相识刚一周,他就必须去英国了。后来他找了个演讲之类的借口转去荷兰,其实只是为了再跟我见面。于是我们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通神学会总部待了几天,可能是一个周末或不到一周,然后他又回印度去了。
艾芙琳娜·布劳:那段时间,克里希那穆提谈及他的工作了吗?
海伦·诺斯:是的,工作让他十分焦虑。他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他看到那些工作就在他面前,他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他还经历过一段非常低落的时期。
艾芙琳娜·布劳:他是不是因为自身角色不确定而感到心神不安?
海伦·诺斯:是的,他担心那些人们要求过多,而他无法给予。
艾芙琳娜·布劳:我想这应该发生在1923年,你和克里希那穆提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的埃尔瓦尔德(Ehrwald)。而所谓的“转化过程”又发生了。
海伦·诺斯:没错。
艾芙琳娜·布劳:你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形吗?海伦·诺斯:可以。在埃尔瓦尔德的时候,我每个夜晚都和他在一起。
艾芙琳娜·布劳:是在那些体验发作的期间吗?
海伦·诺斯:是发作刚刚开始。尼亚给艾米莉女士、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写信,说了曾经在奥哈伊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会不会再次发生。
艾芙琳娜·布劳:大约一年前他在奥哈伊经历的“胡椒树体验”此时达到了顶点。
海伦·诺斯:是的,在埃尔瓦尔德复发了,我被叫过去帮忙。
艾芙琳娜·布劳:你能描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海伦·诺斯:那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坐在阳台上,看着山峦。克里希那吉和尼亚会唱颂,我们便唱歌或唱祷文。过了一会儿,显然克里希那吉感觉身体受到了扰动,于是他起身离开大家。
艾芙琳娜·布劳:具体是怎么表现的?
海伦·诺斯:他浑身发烫,感到不安。他和尼亚先进屋了,一会儿尼亚又叫我进去。我进去坐下,握着他的手。他明显有疼痛感,他很悲伤,并不住叫喊。目睹和经历这一切让我很难过,我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他每个晚上都发作一次。我保存了一本日记,记录了那段与他相处的日日夜夜。
艾芙琳娜·布劳:只在晚上发生吗?
海伦·诺斯:是的。他本来看起来很快乐,甚至有些傻乎乎的,但突然他会陷入到那种看上去像是失控的状态,似乎完全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他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艾芙琳娜·布劳:眼下有一些关于灵魂出窍体验的讨论,你觉得他是灵魂出窍吗?
海伦·诺斯:不是的。那很大程度上是在体内发生的变化,是肉身在经历这种非常剧烈的体验。有时候似乎不是克里希那吉,而是一个小男孩——一个几乎只有三四岁的小男孩——的“肉身”在承受痛苦,他甚至对克里希那吉尖叫,说:“离开,我比你更能处理好现在的情况。”那是奇怪的双重人格,克里希那吉会回来对这个小“肉身”说话,他们会交谈。
艾芙琳娜·布劳:是两个不同的嗓音吗?小孩和年轻男子?海伦·诺斯:对。年轻男子会感到有人降临到他体内,照看他,帮助他,但也可能是让他痛苦。尼亚和我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尼亚坐在角落里,我坐在克里希那吉身边,半扶半抱着他。尼亚和我都没有眼通,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一种神奇祝福的降临,仿佛从远山缓缓来到这个房间,将信息传给尼亚、我和克里希那吉。
艾芙琳娜·布劳:那些信息是怎么传递的?
海伦·诺斯:通过克里希那吉说出的。尼亚或我在黑暗中努力将它们飞速记下。这些信息,有些是给尼亚的,有些是给我的,还有些是给克里希那吉自己的。
艾芙琳娜·布劳:是什么样的信息?
海伦·诺斯: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以及那些痛苦意味着什么。
艾芙琳娜·布劳:那些痛苦意味着什么呢?
海伦·诺斯:我们认为那意味着拙火的启动以及通道的清理,是神主降临在克里希那吉身上,为他施加善意的影响。屋里好像除了我、尼亚与克里希那吉之外,还有着另一个小小的完全不同的存在体,这个小“肉身”是如此稚嫩,如此甜蜜,如此可人,它和克里希那吉在互相交谈和争论着。
艾芙琳娜·布劳:他们争论些什么呢?
海伦·诺斯:年幼的声音说:“我比你更知道怎么处理这疼痛,你待在外面。”但克里希那吉进到里面,发出尖叫,然后又跌出来……我确信住在两层楼下的照料房子的农民一定听到了喊声,约翰·考德斯告诉他们说他犯了癫痫。
艾芙琳娜·布劳:你觉得像是癫痫发作吗?
海伦·诺斯:我那时对癫痫一无所知,但是我相信那是一场深奥的耐力测试。
艾芙琳娜·布劳: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海伦·诺斯:我不知道。我对此全无意见,因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艾芙琳娜·布劳:这一系列事件让克里希那穆提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海伦·诺斯:他完全可以是个正常人。我们很难相信他和发作时是同一个人。
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挣扎,因为我对权威、灌输或怂恿感到不满;我想自己去探索,所以自然需要经历痛苦才能找到。
——《是谁带来了真理?》,1927年
如果你狂热地爱着真理,而且完全是为了它本身才爱着它,那么你爱的确是真理。如果真理是一种安慰,而你有了那种安慰,那么你的愿望只是与他人分享……
——《智慧池》(ThePoolofWisdom),1927年
那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也不是一个需要跨越世界尽头才能抵达的住所。你必须寻找打开天堂和极乐花园大门的钥匙;这钥匙就是你的直觉,带着它,你能进入天堂,永远地住在极乐花园里。
——《智慧池》,1927年
艾芙琳娜·布劳:他醒了之后记得这一切吗?
海伦·诺斯:记住的不多。
艾芙琳娜·布劳:他有疼痛感,或疼痛舒解的感觉吗?
海伦·诺斯:疼痛要么出现,要么彻底消失。有时尼亚半夜把我叫醒,说:“你最好过来,克里希那吉需要你。”我就会过去陪他。我不知道那是克里希那吉还是小男孩,不过我很愿意去陪他。这种情况在埃尔瓦尔德继续了一个多月。后来,他说服我跟他回澳大利亚,不再留下来学小提琴。于是我回到维也纳去取我的小提琴和乐谱,与那里的人告别,又回家说服我父母让我去澳大利亚。那之后不久我还和他在一起。在从南安普顿到纽约的船上,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仍经历着那种痛苦。在我的记忆里,他以后好像再没发作过这么久了。
艾芙琳娜·布劳:为期一个月,那确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海伦·诺斯:他需要并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尼亚就给我们安排了相邻的客舱,我就和他在一起。
艾芙琳娜·布劳:所以有人说你有一种特殊的影响力。海伦·诺斯:我明显是一个特殊的角色。
艾芙琳娜·布劳:在你陪他经历痛苦的过程中,他对你表白过爱意吗?
海伦·诺斯:表白过。
艾芙琳娜·布劳:所以说他对你的爱并没有被这个转化过程破坏?
海伦·诺斯:没有。事实上可能还加强了,因为我跟他很亲近。
艾芙琳娜·布劳:你们在一起待了多久?
海伦·诺斯:他安排另一位年轻女子露丝·罗伯茨和我单独前往悉尼。他继续给我写信,希望我一切顺利。后来因为尼亚身体不好,需要离开印度,克里希那吉与他在前往奥哈伊的途中来到悉尼。克里希那吉在悉尼并不受李德拜特欢迎。
艾芙琳娜·布劳:为什么呢?
海伦·诺斯:李德拜特并不理解发生在克里希那吉身上的转化过程,说那种事情从没在他自己身上发生过,也从没在贝赞特夫人身上发生过。他对克里希那吉非常冷淡,让他在悉尼庄园的大厅里一直等着。而克里希那吉非常挂念尼亚,理当如此,因为尼亚时日无多。
艾芙琳娜·布劳:我想听你描述一下克里希那穆提与他弟弟之间的关系。
海伦·诺斯:他们之间有着亲密、温馨、甜蜜和弥足珍贵的关系。我认为尼亚是他在这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他也爱贝赞特夫人,爱艾米莉女士,同时也爱我,但尼亚是所有人里与他最亲密的,可以说就是他的一部分。尼亚在很多方面帮助了他。
艾芙琳娜·布劳:你从没觉得他们之间存在嫉妒或所谓的手足矛盾?
海伦·诺斯:从来没有。他们是非常相爱的兄弟,彼此非常感激。那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关系。
艾芙琳娜·布劳:那时候克里希那穆提与安妮·贝赞特的关系如何呢?
海伦·诺斯:他对她非常爱戴,非常温柔,非常忠诚。
艾芙琳娜·布劳: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他过于埋头工作。海伦·诺斯:没错。我可以理解他。
艾芙琳娜·布劳:你第一次发现克里希那穆提与通神学会之间出现分裂迹象是在什么时候呢?
海伦·诺斯:大概在他和尼亚第二次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出现分裂的苗头了。开始是因为李德拜特孤立他,但是他顾不上这些,他一心挂念尼亚的健康。
艾芙琳娜·布劳:那段时间他有明显的改变,他的文字越来越开放,他变得越发独立,在人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那时你和克里希那穆提订婚了吗?
海伦·诺斯:不,没有。首先,他对自己的使命非常清楚,我自己也隐隐有所了解。贝赞特夫人也说了很多我们非常亲密,可以一起成长一起工作之类的话,但是不会发生订婚这样的事情。
艾芙琳娜·布劳:人们显然认为婚姻会让他对自己的使命分心。
海伦·诺斯:噢,当然。这甚至被明确写下来了。那时他在奥哈伊,我觉得好像有智者在提醒他“你走得太远了”,从此奠定了他的超然态度。我的家人那时希望我从澳大利亚回去,我不情愿地离开澳大利亚。克里希那穆提在美国的圣巴巴拉(SantaBarbara)接我,开车带我去奥哈伊。他的亲切与深情一如既往,但是有一些东西不同了。我感觉我们的亲密关系结束了。我在阿亚维哈拉停留了大概一周,他送我去坐火车。我们仍然是很亲近的朋友,彼此相爱,但仅此而已。
艾芙琳娜·布劳:那段时间你对他的教诲有什么想法?你对那些教诲感兴趣吗?
海伦·诺斯:他的教诲是“活在当下”。我完全接受了它,并将其改造为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贯彻至今。我从未否认过任何他说过或写过的东西。我从未将它们抛之脑后,并把它们融入自己的生活。
和其他人一样,克里希那穆提也曾追寻、服从和崇拜过,但是随着时光流逝,随着痛苦降临,他想去探寻和理解真相——隐藏在画面背后、夕阳背后、影像背后、一切哲学背后、一切宗教背后、一切派别背后、一切组织背后的真相。他一直被禁锢在假相和幻象之中,直到他逐渐超越了所有带着局限和束缚的圣坛,以及所有要求膜拜的神。超越这些之后,他抵达这样一种境界:所有宗教之间都是圆融的,所有情感都是无漏的,所有崇拜都被终止,所有欲望都被止息,孤立的自我经由消亡实现净化。我已经经过那些阶段,能够用自己的所知与权威对话,并能够授予你们这些知识和经验。
——《是谁带来了真理?》,1927年

明星社的队伍日益壮大,会员不仅覆盖印度、英国、欧洲和美国,还有拉丁美洲。克里希那穆提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世界各地,结交了许多终生挚友。他们对他的尊敬从未消退。
克里希那穆提早年在洛杉矶遇到一位年轻人,后来成为他的终生挚友之一。他叫希尼·菲尔德,是一位外交官,也是多部好莱坞电影剧本的作者。他出生于哥斯达黎加,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哥斯达黎加人。他的父母是哥斯达黎加明星社的创建者,也是克里希那穆提兄弟俩的朋友。
艾芙琳娜·布劳:那些年你在美国一直听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你去过其他国家听他演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