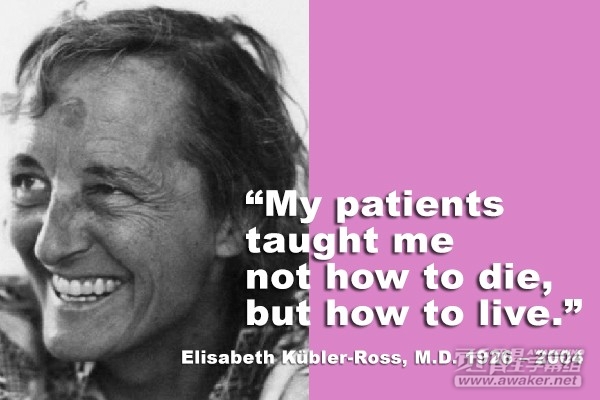
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不详。
对不少从事临终照顾的人士来说,伊莉萨白.库伯勒.罗斯医 (Elisabeth Kübler-Ross)是位重要人物。这位生于瑞士的心理医生对死亡的研究,把西方医学对濒死病患者的处理从阴暗冰冷中带回阳光之下。她透过文字和行为,把关怀一词变成给濒死病人的处方药物,也把同理心加入了照料他们的医学程序。
在六十年代,罗斯医生借着对两百多位绝症病人的心理分析,归纳了他们在面对生命中最大的坏消息后的五个阶段: 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抑郁(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
罗斯医生的著作《On Death and Dying(中译死亡与濒死》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为医学界带来震撼。这本文献和她之后的多本着作,探讨了由濒死时魂魄出窍到死而复生的现象。在怎样面对死亡这一大难题上,替我们开拓了宗教以外的一片天空,也构成现代生死学的基础。
罗斯医生认为死亡是自然现象,本身并不可怕。反之现代西方文化对死亡加上虚伪的掩饰和造作,反而令大众失去自然地面对死亡的机会。她举例说墨西哥就有着对死亡处之泰然的特质,他们只要兴之所至,就会带同食物到亲人坟前,像处身家中般和死者闲话家常。罗斯医生对童年在瑞士时一位邻居的守灵仪式印象深刻。罗斯医生的父亲和其他亲友一般,可以随意触踫死者和跟他说话,整个仪式完全没有现代丧礼要为死者穿上丝质丧服、躺进用绸缎软垫覆盖的棺木和面上涂上胭脂等的人工造作。这些细节,从罗斯医生的角度,是加深现代人对死亡的隔阂的主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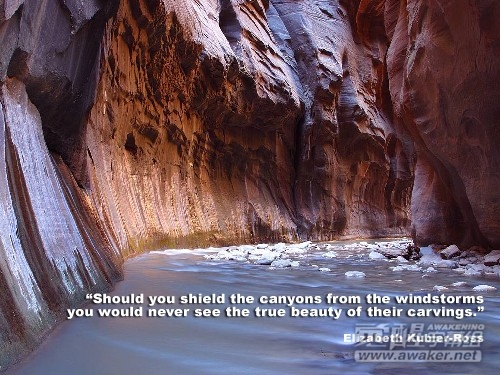
从多年和死亡交往的经验,罗斯医生察觉,只要病人在生时依照自己的意向而活,日子充实,事事尽力而为,没有留下悔疚,多会安详的离开世界。反之,背负着未能完成别人对你期望而离开的病人,往往显得十分痛苦和哀伤。

怎样面对病重的亲人?罗斯医生认为诚实和爱,是处理的两大基石。不要回避病者的问题,但不要为他们未问的先行作答。千万不要自作诚实好人,把自以为的真相公开令他们希望幻灭。病人未提出的原因可能是未能接受答案。而希望,正正是我们生存下去的最大动力。在最后阶段时,在病人周围组成一个用爱织成的支持网,尽量答应他们的要求。无论是选择在家中离世、转到宁养医院,甚至喝一杯咖啡、抽一根烟,在可能情况下,应尽量配合。
罗斯医生除了学术研究外,也创办了「和平之家」(Shanti Nilaya, Home of Peace),一所为濒死病人设立的疗养设施。一九八五年,她也计划在美国维珍尼亚州设立专为艾滋病童而设的宁养医院,但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而告吹。一九九四年,她的住所更被纵火而烧毁。
伊莉萨白.库伯勒.罗斯生长于瑞士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小康之家,母亲在一九二六年诞下包括她姊姊和妹妹的三胞胎。
罗斯五岁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当时医生觉得她生存的机会渺汒,虽然后来罗斯奇迹的康复,但医院阴暗、冷漠的环境,在她心内留下不能磨灭的阴影。十三岁时,妹妹也患上同一症状,令罗斯立志要当一位医生,但父亲却极力反对,要她将来留在家族生意工作。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了「国际和平志愿工作团」。由于瑞士在大战期间维持中立,罗斯未曾目睹战争的可怕。波兰的迈坦尼克集中营(Majdanek
Concentration Camp)的一段经历,是罗斯医生人生的转折点。

在一次访问中,罗斯医生向美国脊医权威Daniel Redwood,说出这个改变一生,令她投身心理学的经历:
我知道纳綷在迈坦尼克的毒气室中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儿童,但我在营房的墙上,见到的却是他们留下一张又一张的蝴蝶图画。我清楚这些画是小孩在知道再也见不到父母、亲人后画下的,这个境象给我很大的震撼,同时也带来很大的疑惑。
我当年只是一个在无风无浪的瑞士成长的一个年轻女孩,对人性的丑恶认识不深,迈坦尼克和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和无法理解。
杀死千万儿童的凶手,本身也是普通人,也会为自己孩子的健康担忧,然而却可以日复日的作出杀人的冷血行为?
当日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在集中营当义工的犹太女孩歌妲,她的父母、祖父母、兄弟和姊妹都被送进毒气室。到她被安排进入毒气室的那天,却因为当天被安排的人数已经超出负荷,临时把她从队伍中抽出来。但因为她的编号已被列入死者名单,一直未有再被送回毒气室,奇迹地逃过一劫。
歌妲在集中营渡过余下的日子,她立誓要尽余生之力把目睹的恶行公诸于世。
当盟军解放迈坦尼克时,歌妲却对自己说:
“若我在以后的日子都花在形容丑恶上,我和希特拉就会无甚分别。从我口中出来的,全部都是仇恨和恶毒的种子。”
歌妲告诉我她向上帝保证,如果一天未能宽恕希特拉,她一天都会留在营中。当她离开迈坦尼克时,要带着营中岁月给她的教训。
临别时,她再和我说:
“妳可能还未清楚,在所有人当中,存在着一个希特拉!”
她的意思是,我们必需先承认心中存在着邪恶,然后才能把它驱除,做一个真正的善人。
听毕她的说话,我却在想:
“她肯定有点不正常,我的心里怎会藏着一个希特拉。”
几天后,因为我染上风寒病,我要离开迈坦尼克。在不断需要转乘便车的旅途中,因为病情加剧和三天未曾进食,我最后无法回到瑞士,被发现昏迷在德国的一处森林中。在医院里,我突然醒觉,在那三天的行程中,若身边经过一位带着面包的儿童,我必定会把面包夺走。
在剎那的顿悟后我对自己说:
“我完全明白歌妲的意思,我心中的确住着一位希特拉。” 随着处境的逆转,生出邪恶的念头是自然的事。
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回到瑞士后我和自己说要进入医学院,我要清楚了解是什么把纯真儿童变成纳綷恶魔的原因。
迈坦尼克的蝴蝶代表什么?在罗斯医生的晚年她得到了答案:
就像蝴蝶破茧而出,死亡令人类的精神蜕变。怎样从转化中悟出道理而变得关爱别人,就是我们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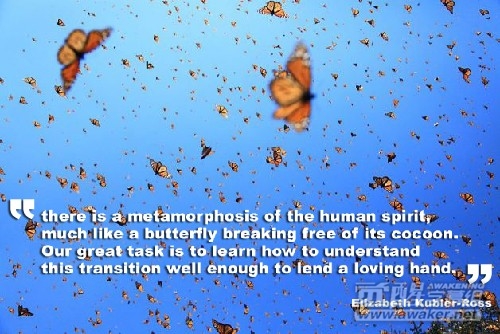
一九九五年,罗斯医生因为一连串的中风令她左半身瘫痪,九年前的今天,参透生死的她在阿里桑那州的家中安详离世。
罗斯医生生前曾说她清楚自己死后的去向,但在到达最后归宿之前,她会先在银河上唱歌跳舞。


